我以为我知道悲伤是什么,但现在我意识到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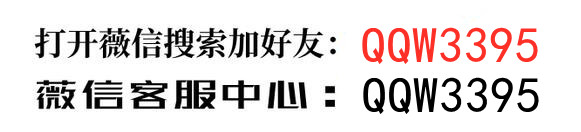
我爸爸去世已经五个月了。
让我更正一下:我父亲去世已经五个月了。我不得不使用这个词——死——因为我的大脑仍然拒绝相信它。

他的死是突然而意外的,后果是残酷的。
我原以为身体上的症状会很快出现,但它们确实出现了,而且大多数症状一直没有消退。疲惫是如此强烈,你可以感觉到你的骨头和脑雾是如此解除武装,使工作无法管理。然后是压力引起的反流、失眠、无法控制的哭泣和食欲不振。
情感上的影响也同样普遍。每天,我的大脑都在努力理解我被迫过的这种新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不能去找爸爸寻求建议,不能和他一起庆祝里程碑,也不能吃他那著名的千层面。
我得重新认识没有父亲的我是谁。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孤立。
但是悲伤有一个我没有准备好的副作用,一个二次的和复合的损失,它很容易地消耗了我——对我的人际关系的影响。
父亲去世几周后,一位朋友给我发短信说:“我很抱歉,你还是这么难过。”
“我相信你处理得很好,”一位表亲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你必须独自经历,”一位同事一边喝咖啡一边说。
这种说法与那些主动提出的陈词滥调的建议——“坚强起来”、“乘风破浪”、“时间会治愈一切”——相伴而生,但与人们自己的死亡经历相比,这还没有那么糟糕:他们年迈的父母、他们在新闻中看到的人、家里的狗。
我不应该抱怨。他们努力伸出手来,把一些话串在一起。他们在努力,这是我在我的圈子里不能说的。
无线电静默已经司空见惯。一些人参加了葬礼,然后就不再联系了,好像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还有一些人花时间来拜访,但一个问题也没有问,他们认为这会让我更难过。大多数人拒绝说出我父亲的名字,在我提起他的时候避免眼神接触,或者努力控制自己的眼泪。
但我不能责怪任何人。这些反应只是我们西方文化的副产品。我们想要相信自己是不朽的,坏事不会发生在好人身上,我们可以避免悲剧。
我们愿意相信衰老是生命的必要条件,而实际上它是一种奢侈品。
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责怪别人,因为我对我的朋友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她也在25岁左右失去了父亲。
我参加了她的葬礼,给她做饭,每周给她发短信,但后来生活接管了我,我停止了努力。我想相信别人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但说实话,我只是在保护自己免受她难以承受的痛苦,假装这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它做到了。
年轻人不知道如何谈论悲伤。
就像许多其他在相当多的特权下长大的澳大利亚年轻人一样——我所说的特权是指我们的低死亡率、高预期寿命和无障碍的公共卫生系统——我最初的悲伤参考框架是我十几岁时祖父的去世。
当悲伤刺痛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患有癌症,多年来一直忍受着痛苦。他死亡的自然顺序是有道理的,社会叙事让我准备好接受它。
但年轻时失去父母并不罕见。每年在澳大利亚,大约每2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会在18岁之前经历父母的死亡。与这种改变生活的损失作斗争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如果没有适当的护理,会对我们的健康、幸福和生产力产生严重影响。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柳叶刀》精神病学委员会最近的报告发现,精神疾病至少占10至24岁人群总体疾病负担的45%,但全球卫生预算中只有2%用于有针对性的护理。即使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富裕国家,也只有不到一半的需求得到了解决。
我很自豪能成为年轻一代的一员,他们公开谈论心理健康,优先考虑幸福,不怕问我们最需要什么。我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把悲伤带进这个圈子。
我知道我不能代表所有人,悲伤是复杂的,但悲伤的年轻人不应该有责任自我辩护。我们害怕、迷茫、疲惫——我们需要朋友、亲戚、同事和管理机构为我们挺身而出。
我们需要你和我们坐在一起,创造空间,让我们试着理解我们的损失,不管你感到多么不舒服或尴尬,因为负担太沉重了。
我们需要你们向我们提问,记住我们所爱的人,公开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他们的世界。
我们需要你主动签到,并接受取消的计划或不稳定的沟通,因为我们仍在学习勇敢面对新的常态。
我们需要你放弃我们不想说话的假设或者你提起我们的悲伤会让我们感到不安的假设,因为我们不能一直感到如此孤立。
我们需要成年人和更广泛的系统来模仿这种行为,并就死亡展开健康的对话,因为最终,悲伤会影响我们所有人。
Ruby Kraner-Tucci是墨尔本人Sed作家和记者。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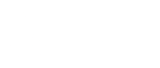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