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生忽略了我的产后症状我开始自己治疗它们——然后上瘾了

我是一个正在康复的瘾君子,今年早些时候,我出版了一本关于我对酒精和药物上瘾的回忆录。几周前,我在播客上接受采访,主持人问我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上瘾了——具体来说,是为什么我第一次开始服用安必恩,这种药让我上瘾。
以前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想我生来就是个瘾君子,对某种物质上瘾,对我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次,这个问题对我的冲击不同。
“说实话,”我说,在我确信那是一段令人不舒服的长时间沉默之后,“我想我是在用安必恩治疗未确诊的产后焦虑。我认为,如果没有产后和其他影响女性的问题带来的耻辱感,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自我治疗,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8月4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Zurzuvae (zuranolone的品牌名),这是第一种专门用于治疗产后抑郁症的口服药物。这种药与大多数其他抗抑郁药不同,因为它起效快,服用时间短——只要14天。此外,由于祖拉诺酮是一种药丸,服用起来比fda批准的唯一一种治疗产后抑郁症的药物——静脉注射布雷沙诺酮(brexanolone)(售价3.4万美元)更方便。
显然,以药丸的形式进行治疗将改变游戏规则。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一宣布引发了急需的关于这种影响八分之一新妈妈的疾病的讨论。26年前我儿子出生时还没有这样的对话。
“你觉得我可能有产后抑郁症吗?”
那是1999年12月,我坐在产科医生的办公室里,穿着一件粗糙的纸袍子,弄痛了我刚吃完母乳的乳头。说完这些话后,我短暂地闭上眼睛,不安地动了动身子。我希望他会笑着说我错了。像我这样年轻又乐观的人不可能有产后综合症。
尽管我鼓起勇气说出了这句话,但我不知道如果他答应了我该怎么办。因为如果他说是的,那就意味着那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那我就是有缺陷的。
六周前,我生了两年内的第二次孩子。1998年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我的情绪非常激动,但我的身体感觉很好。我很容易就恢复过来了,很快又回到了每周锻炼五天的生活和安排得满满的社交生活。
我真不明白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布特。这很容易。
我对产后的了解是在新闻上看到的。据报道,自杀或自杀婴儿的妇女通常患有这种疾病。这些女性都是典型的白人,情绪明显不稳定。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一个年轻妈妈承认自己有过产后经历。当我们的黑人妈妈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时,感觉像是在评判,就像:“你听说丽莎的事了吗?自从有了孩子,她过得很艰难,可怜的孩子。”
可怜的莉莎。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这些没有“遇到困难”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更好的母亲(和人)。
我的第二次怀孕就像第一次一样,无忧无虑,一帆风顺。我的分娩过程很短暂(推了三下),几乎无痛。但回家没几天,我就开始接受新情况的现实。我是一个可爱的新生儿和一个同样可爱(但非常活跃)的幼儿的母亲,他们两个一次都睡不了几个小时。
整整一个星期几乎没怎么睡觉,我模糊地意识到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响起了警钟。虽然我没有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但我被焦虑所吞噬。
我知道我应该在孩子睡觉的时候睡觉,但我就是睡不着。一想到他们会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就睡不着。我总是用耳朵环视着房子,听着醒来前最微弱的呜咽声。
一开始,我没有想到我可能要处理产后问题。我没有感到无精打采或无精打采。不像那些新闻里的女人,我爱我的孩子,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他们或我自己。我从未听说过产后焦虑,也不知道它影响着多达20%的新妈妈。
在产后六周的预约之前,我去做了指甲和头发。(我两次在生产前都做了脱毛——只是为了告诉你我的头在哪里。)我想如果我看起来更好,我可能会感觉更好,如果我诚实的话,我想给我的产科医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怀孕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告诉我,我是他“最容易的病人”。他甚至向护士们吹嘘。
我急切地接受了这个角色。我努力快速减掉婴儿体重,确保我总是保持清醒(无论发生什么),我没有抱怨或扮演受害者。我不想在产科医生面前失去那种“比别人好”的地位。
但我迫切希望内心的警铃不再响起。
“你为什么觉得你有产后综合症?”
“我不知道。孩子们睡觉的时候我睡不着,我似乎无法放松,就像以前一样。”
“你觉得食欲不振吗?”情绪波动?”
“No.”
“你会感到绝望或大哭吗?”
“不,不是那样的。”
我感到全身都松了一口气。我没有这些症状,所以我不能产后。
“你已经连续生了两个孩子了,”他笑着说。“让我们给你的身体一个恢复的机会,然后看看你在哪里,好吗?”与此同时,如果你很难放松,就试试晚上喝一杯葡萄酒。你哺乳的时候应该没问题。”
在回家的车里,我责备自己没有告诉他闹钟响了,也没有告诉他我过度警惕的感觉。
医生给你的金星更重要吗比变得更好更重要吗?
几个月后,我的主治医生第一次给我开了安必恩。我告诉他,我的孩子们还没睡,我也没睡(这件事我一直瞒着别人)。我没有提到的是,警钟比以前更响了,我开始感到绝望。
就在我第一次服用安必恩的那一刻,我的警铃就响了。我钻进被窝,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柔软的宁静中。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精神焕发,没有一点药物的后遗症。我觉得自己像个超级英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想。只要我有这些药(永远),我就可以出现在我的家人面前。
我陷入毒瘾的过程就像海明威关于破产的那句话——“逐渐地,然后突然地”。我开始每晚服用一片安必恩来治疗我的病情。六年过去了,我在任何给定的24小时内都要服用多达10粒安必恩。更重要的是,我的焦虑和失眠更严重了。
2008年7月,我开始接受治疗以寻求帮助。但是,尽管我接受了包括治疗师在内的几位医疗专业人士的评估,但没有人敢说,我对安必恩上瘾是在我开始自我治疗未确诊的产后疾病时开始的。
研究人员发现,与没有抑郁症状的产后妇女相比,产后妇女滥用药物的风险更大。相反,有药物滥用史的女性更有可能出现产后抑郁症的症状。
我甚至羞于大声说出“产后”这个词——我想这样做会让我成为一个不称职的妈妈。当我的医生解除了我的症状后,我开始用安必恩治疗产后焦虑。
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到关于Zurzuvae的文章时,我在想:如果这种药在我的孩子出生后就能买到呢?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吗?我还会成为瘾君子吗?
怀孕和产后被认为是抑郁症状的危险时期。再加上上瘾,你就酿成了悲剧。只要我们害怕说出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就更有可能使用药物进行自我治疗。
希望Zurzuvae只是一个姗姗来迟的趋势的开始,旨在给新妈妈和她们的孩子一个更好生活的机会。
需要药物使用障碍或精神健康问题的帮助?在美国,拨打800-662-HELP(4357)获得SAMHSA全国帮助热线。
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吗你想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什么故事?找出我们在这里需要什么,然后给我们发一份建议书。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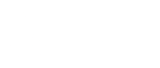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