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布鲁特斯”杀死埃隆·马斯克的“凯撒”


在华盛顿邮报》周一的头条是:马斯克和杜罗夫正面临监管机构的报复。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控制”埃隆·马斯克的文章,建议“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应该用逮捕来威胁马斯克,就像帕维尔·杜罗夫最近在巴黎遭遇的那样。
现在大家都应该清楚了,“战争”已经爆发了。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相反,人们对打击“极右翼”及其互联网用户(即那些传播“虚假信息”或“威胁”广泛的“认知基础设施”(也就是说,人们的想法!)的错误信息)的前景明显感到高兴。
毫无疑问,统治阶层非常愤怒;他们感到愤怒的是,他们的技术专长和对“几乎所有事情”的共识正在被“可悲的人”所唾弃。“领导人”警告说,扰乱数字“素养”的网络“行为者”将受到起诉、定罪和罚款。
Frank Furedi教授指出:
福瑞迪解释说,就斯塔默而言,民粹主义是对整个欧洲技术官僚的权力的威胁: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人歇斯底里地反民粹主义呢?答案是,后者知道,他们已经与本国人民的价值观和尊重割裂开来,他们受到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严重挑战只是时间问题。
这一现实在上周末的德国非常明显,非建制党(即非Staatsparteien)政党——加起来——在th
林根州获得了60%的选票,在萨克森州获得了46%的选票。国家党(被提名的建制政党)选择将自己描述为“民主的”,并将“其他”贴上“民粹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标签。官方媒体甚至暗示,更重要的是“民主”投票;而不是非staatsparteen的选票,所以拥有最多staatsparteen选票的政党应该在th
林根组建政府。
这些政党通力合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和其他非建制政党排除在议会事务之外——例如,不让它们进入关键的议会委员会,并实施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
这让人想起了伟大诗人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被法国文学院(academie francaise)拒之门外的故事——拒之不下22次。第一次申请时,他从当时最伟大的两位文学家拉马丁和夏多布里昂那里获得了2票(总共39票)。当时一位机智的妇女评论说:“如果我们计算一下选票,雨果先生会当选;但我们正在数。”
为什么要战争?
因为,2016年美国大选后,美国政治幕后人士指责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造成了糟糕的选举结果。反建制派的特朗普实际上赢得了美国大选;博索纳罗也赢了,法拉奇飙升,莫迪再次获胜,还有英国脱欧等等。
选举很快就被宣布失控,产生了奇怪的“赢家”。这些不受欢迎的结果威胁到根深蒂固的结构,这些结构既投射又维护了美国在全球长期存在的寡头利益,让他们(哦,太恐怖了!)接受选民的审查。
到2023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开始刊登题为《选举不利于民主》(Elections Are Bad for Democracy)的文章。
罗德·布拉戈耶维奇(Rod Blagojevich)今年早些时候在《华尔街日报》(WSJ)上解释了这个体系崩溃的要点:
问题是,拜登痴呆症的暴露已经从系统中揭开了面具。
芝加哥模式与欧盟民主的运作方式并无太大不同。数百万人参加了最近的欧洲议会选举;“非国家政党”取得了重大成功。发出的信息很明确——但什么都没有改变。
文化战争
正如迈克·本茨(Mike Benz)所详细描述的那样,2016年代表着文化战争的开始。作为一个完全的局外人,特朗普冲破了体制的护栏,赢得了总统职位。人们认为,民粹主义和“虚假信息”是原因所在。到2017年,北约将“虚假信息”描述为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
被认定为民粹主义的运动不仅被认为对其对手的政策怀有敌意,而且也被认为对其价值观怀有敌意。
为了应对这一威胁,奔驰解释了幕后老板们是如何采取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花招”:他们说,“民主”不再被定义为一种共识——即被统治者之间的一致决心;相反,它被定义为不是由个人,而是由支持民主的机构形成的一致的“立场”。
一旦重新定义为“支持机构的结盟”,民主重新表述的第二个“扭曲”就被添加进来了。建制派已经预见到这样一种风险:如果对民粹主义展开一场直接的信息战,他们自己就会被描绘成专制的、实行自上而下的审查制度。
奔驰认为,解决如何开展反民粹主义运动这一难题的办法在于“全社会”概念的起源,即媒体、有影响力的人、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媒体将被召集起来,并受到压力,加入一个明显有机的、自下而上的审查联盟,专注于民粹主义和虚假信息的祸害。
这种方法——政府站在审查过程的“一个”之外——似乎为政府直接参与提供了合理的否认;当局的专制行为。
数十亿美元被花费在建立这个反虚假信息生态系统上,使其看起来像是民间社会自发产生的产物,而不是波将金式的伪装。
举办了研讨会,培训记者了解国土安全虚假信息的最佳做法和保障措施——发现、减轻、驳回和转移注意力。本茨透露,研究资金被输送到大约60所大学,以建立“虚假信息实验室”。
这里的关键是,“整个社会”框架可以促进融合回到长期框架的政策主流和很大程度上不言而喻的(有时是秘密的)外交政策的基石结构-在这个基础上,许多关键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被杠杆化。
尽管如此,一种表面上平淡无奇的、专注于“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结盟,将允许这些持久的结构重新整合到外交政策中(对俄罗斯的敌意;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对伊朗的反感)将被重新表述为对民粹主义者的一记恰当的口头耳光。
战争可能升级;它可能不会以一个虚假信息的生态系统结束。《纽约时报》在7月份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了第一修正案是如何失去控制的,8月份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宪法是神圣的》的文章。它也危险吗?
目前,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不负责任的”亿万富翁:帕维尔·杜罗夫(Pavel Durov)、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他的X平台。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生存与否将对战争的这一方面至关重要: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 Act)一直被认为是马斯克的“凯撒”的“布鲁特斯”。
纵观历史,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人已经变得危险地蔑视他们的人民。镇压通常是第一反应。冷酷的现实是,最近法国、德国、英国和欧洲议会的选举显示出人们对建制派的极度不信任和厌恶。
一个宣传的生态系统并不能恢复信任。它侵蚀了它。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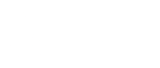
最新评论